最新看影片《記者甘遠志》有感
更新時間:2023-08-13 21:25:36 高考知識網 www.comonvc.cn篇一:看影片《記者甘遠志》有感
他靜佇在那里,頷首微笑,默默目送一個個戰友從這里奔向新聞現場。他的目光,溫暖而堅定地伸向遠方;他的四周,熱帶灌木叢青翠欲滴。
“你看到我的時候,我在報紙上;你看不到我的時候,我在路上。”每天從塑像身邊經過的同事們,仿佛又聽見他那熾熱的話語,在耳邊深情響起。
在39年的年輕生命里,在最后3年的新聞戰場上,甘遠志用自己的故事告訴人們:人生重要的并不在于有多長,而是在于有多好。
“記者是這個世界上最辛苦的職業之一,也是最快樂的職業之一。”
來海南日報之前,甘遠志在四川南充日報當過記者,在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旗下的《新世紀》雜志任過主編。2001年,因《新世紀》轉軌,甘遠志調入海南日報社。當時,他已經36歲。
再次進入新聞界,他的愿望是從基層“揀感覺”,將宏觀經濟學觀察方式落到經濟生活觀察之中。“記者不到基層,怎么能寫出新聞,怎么能當好記者?”他執意向報社提出,從理論評論部調到基層駐站。
那時候,東方記者站是一間狹小的房間,書桌簡陋,灰塵滿屋,沒有電腦,沒有交通工具,老舊空調轟轟作響。最先接待甘遠志的東方市委宣傳部副部長符巍回憶,“他一點也不畏縮,沒有半句怨言。”
安頓下來后,他先從資料圖冊上熟悉東方。接下來,他和符巍頂著烈日和暴雨,一起乘坐班車或摩托車,進廠礦企業、跑學校醫院、下田間地頭,他們的足跡幾乎踏遍了東方大地。累了,在樹底下歇歇;餓了,在路邊小攤吃碗湯粉;沒有電腦,就用手寫再發傳真。
8月13日,《“金大田”香蕉跑贏市場》在海南日報頭版刊發。他說,這是他第一次深入海南山區采訪,第一次感受到記者的為人民服務和受人民稱贊的快樂。很快,更多的報道頻頻見報:《東方養蝦不忘環保》、《中海油大化肥工程進展順利》、《小腌瓜挺進大市場》……
8月底9月初,熱帶風暴侵襲東方。他身披雨衣,腳穿拖鞋,不顧大家的勸阻,執意到最危險的地方去采訪。風大雨大,全身濕透,人都站不住,但他仍奔跑在抗洪前線,現場采訪寫稿。除報社要求采寫的3篇稿件,他還采寫了反響強烈的特寫《為了11名民工的生命》、《大壩上的9小時……》和長篇通訊《洪流滔滔顯本色》。
不錯,有新聞的地方就會有記者,還有他們記錄一切的鏡頭與探尋真相的眼睛。
“倘若國家是一條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聞記者就是船頭的?望者。”
3個月后,就在甘遠志準備跑東方最后一個鄉的時候,他被報社硬拉回經濟部接手工業口。隨著省委省政府實施“一省兩地”的發展戰略,工業成為重要報道的行業之一。“我基層還沒跑熟,腦子里還缺很多東西。”這一次,報社沒有同意讓他繼續駐站。
到經濟部后,除工業口外,分到他手里的還有一些“硬梆梆”的部門和行業。但是,他很快就把一些“僵”的東西跑活了,把“生”的東西跑熟了。部門不好打交道,他就一層樓一層樓地竄,一個處一個處地泡;第一次去吵架了,第二次還去,第三次就和吵架人成了朋友……憑扎實的理論素養,別人很快接納了他。在這些行當里,他很快如魚得水。
“哪里有大項目,哪里就有甘遠志;哪里有重大報道,哪里就有甘遠志。”已然成為人們的一種閱讀慣。《洋浦電廠改造工程快馬加鞭》、《走向新型工業的春天》、《2003,海南工業轉折之年》……他寫出的大量經濟報道,不僅普通讀者能看懂,行業專家也非常認同,把他評價為專家型記者。物價,以前是報道空白,他卻挖出了源源的新聞;交通,以前少有報道,他卻發回一篇篇稿子;藥品,以前很少涉足,他卻發現了“富礦”;電力,以前少有問津,他卻把它跑成“熱門”。
“他在報社共工作1095天,刊發稿件多達1051篇。”海南日報新聞研究所的統計數字這樣顯示。如果把這些字一個一個排開,它意味著一個記者的節日、假日、睡眠、吃飯,乃至生命。
“記者這份職業,充滿了激情和理性,交織著希望和失望,時時伴隨著對勇氣的挑戰。”
有人說,認真是一種態度,執著是一種精神。
讓省交通廳特約記者陳濤至今難忘的,是甘遠志為讀者負責的工作作風。2003年2月的一天,中午12點多,陳濤正準備離開辦公室,甘遠志來了,說報社缺頭條。當時,有一份關于農村公路建設方面的材料,陳濤答應吃完午飯幫他找,他卻非要找到材料后才去吃飯。下午,他又到省交通廳來了解投資、建設里程及這些公路項目的分布情況。為證實材料的真實性,他又采訪了廳里有關領導。第二天,《為我省農村全面奔小康助跑???10億元改造建設10條公路》在海南日報頭版頭條刊發。
“吃人家嘴軟,拿人家手短。新聞要是與采訪對象扯不清楚,就喪失了獨立和權威。”他私下里對同事說。
他采訪電力行業,對于推介行業形象、化解用戶的誤解做了不少工作。海南電力公司的領導回憶說,“我們看他經常擠公共汽車采訪,多次請他坐出租車,說給他報銷車票,他總是一笑了之;我們說給他一輛舊車開,他說這樣太麻煩;我們說讓他拿些餐費票報銷,就當他的誤餐補貼,他說自己工資不低,已夠開支。”
其實,他的生活壓力并不小。年邁的父母遠在故鄉南充,妹妹、妹夫下崗多年,一個月工資要寄到幾個地方。妹妹、妹夫想讓他求人找工作,他卻說,“生活上有困難我可以接濟,但工作還要自己想辦法。”這些年,他給妹妹寄了很多錢。現在,妹妹明白了,“原來哥哥是想讓我們通過自己的努力,活得更體面,更有價值。”
他喜歡唱歌,但他不會唱“人情歌”。有一次,在東方采訪之余,他建議去唱唱歌,特約記者卞王玉玨要去安排。他問,“你怎么安排?”對方說,“借你的大名找個買單的還不容易?”他不答應。就這樣,他倆到露天大排檔,花10塊錢盡情地唱了一晚。
“他寫了許多東方化工城的稿,但他從未對我們提過任何要求。他往返東方化工城,也從未讓人用車接送過。”東方化工城特約記者符運煒說。
“有一種小鳥,飛啊飛,累了就睡在風中,它一生只落地一次,那就是它死去的時候。”
他太累,太累了。
2004年5月30日下午,即將奔赴香港參加報道的前一天,妻子陪甘遠志到省文體廳去取機票。那天,他感覺特別累,坐在文體廳辦公室沙發上動彈不得。妻子讓他去醫院檢查,他執意不肯,只在藥店買了點救心丹吃。
第二天中午1點就要飛了,一大早妻子以扣留機票將他“挾持”到省人民醫院檢查。這一檢查,他被送進了重癥監護室。他不干了,爬起來就往外沖,被醫生護士強行拖回病房。妻子回憶,“他像孩子一樣哭了,醫生沒辦法,打了鎮靜劑才把他留在病床上。”
這次發病,他在醫院住了整整兩個星期。出院后他只記住了醫生“心臟沒大事”的話,卻忘記了讓他多休息的囑咐。“報上一天沒有我的名字,心里就有說不出的滋味。”第二天,他又投入到緊張的采訪當中。
“我在大廣壩采訪。”這是遠志留給同事的最后遺言。
9月3日,他隨同省領導到東方調研。此前,他從洋浦到東方化工城,再到大廣壩,幾天里行程已千公里。大廣壩采訪完已是晚上,他堅持留下來連夜寫稿,第二天再回海口。卞王玉玨回憶,剛回房間他就說,今天好困好累。我認識他三年多了,從沒有聽他喊過一聲累。我勸他休息一會吧,注意身體。他說沒事,直到他寫完稿件我們才去吃晚飯。
“生前最后一個早餐,他吃了整整一個多小時,吃飯時他都沒忘記自己是個記者。”卞王玉玨說,“他說大廣壩二期工程惠及東方、昌江和樂東三市縣22個鄉鎮和5個大型國有農、林、牧場,意義太大了,只要工程正式啟動,就可以好好報道。”中午1點多,甘遠志隨報社采訪車返回海口。剛走一段,他突然覺得心口痛,不得已又倒回賓館躺下。誰能料到,這一躺下竟是永訣。
所有的辦法都用上了,卻沒能把他喚醒。診斷書上寫著:心源性猝死。下午3點多,他年輕的生命,以一個記者特有的方式,定格在永遠的39歲,定格在自己熱愛的崗位上。
就用海南日報總編室主任華曉東為他送行的詩句,來結束對甘遠志的回憶吧,因為我們不愿相信他已經遠行:
2025年最新大型紀錄片《一帶一路》觀后感范文2023-08-25 15:57:47
2025年最新微電影《長征在路上》觀后感2023-08-27 10:44:37
2025年最新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微電影長征在路上觀后感2023-08-13 16:03:38
2025年最新家庭教育紀錄片《鏡子》觀后感范文2023-08-13 00:33:06
2025年最新動畫大作《聲之形》觀后感2023-08-26 10:27:35
貴州高考理科347分排名多少 排名多少位次2025-05-22 11:00:51
北京高考456分排名多少 排名多少位次2025-05-22 10:57:01
濟南職業學院對比遼寧機電職業技術學院哪個好 附分數線排名2025-05-22 10:54:45
四川上廣州商學院多少分 分數線及排名2025-05-22 10:51:12
南寧職業技術學院房地產經營與管理專業怎么樣?錄取分數線多少分2025-05-22 10:48:48
貴州高考文科459分排名多少 排名多少位次2025-05-22 10:45:57
重慶科技職業學院電子信息工程技術專業怎么樣?錄取分數線多少分2025-05-22 10:42:15
2025年最新大型紀錄片《一帶一路》觀后感范文2023-08-25 15:57:47
2025年最新微電影《長征在路上》觀后感2023-08-27 10:44:37
2025年最新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微電影長征在路上觀后感2023-08-13 16:03:38
2025年貴州師范大學求是學院錄取結果查詢時間及錄取通知書發放時間郵寄..2023-08-19 01:02:11
貴州師范大學求是學院2025級新生在哪個校區,新生開學報到時間安排2023-08-17 16:05:07
2025年最新大型紀錄片《一帶一路》觀后感范文2023-08-25 15:57:47
精品文章
- 1黨員干部觀看70周年電影中國機長觀..2023-08-27 22:12:11
- 2小學中國機長紀錄片觀后感4篇2023-08-18 23:20:33
- 3大學2025觀看70周年閱兵觀后感三篇2023-08-18 21:00:12
- 4黨員看電影《我和我的祖國》觀后感..2023-08-27 16:43:29
- 5學生觀我和我的祖國觀后感五篇2023-08-12 10:22:25
- 6市單位組織觀國慶70周年閱兵式觀后..2023-08-17 19:17:20
- 7黨員干部看建國70周年閱兵儀式觀后..2023-08-14 16:58:53
- 8我觀看新中國成立70周年閱兵觀后感..2023-08-15 03:22:22
- 92025年高中生寫的閱兵觀后感四篇2023-08-10 21:27:39
- 102025年基層干部觀看70周年閱兵觀后..2023-08-15 16:08:37
圖文推薦

內蒙古高考500至530分左右可以上什么大學
時間:2025-05-22 10:39:38
內蒙古醫科大學對比河北環境工程學院哪個好 附分數線排..
時間:2025-05-22 10:36:19
湖南高考歷史565分排名多少 排名多少位次
時間:2025-05-22 10:32:43
湖北民族大學法學專業怎么樣?錄取分數線多少分
時間:2025-05-22 10:28:51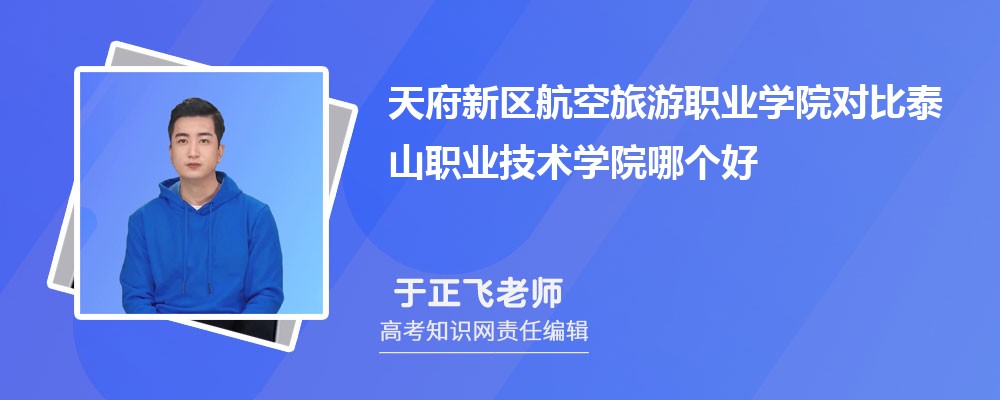
天府新區航空旅游職業學院對比泰山職業技術學院哪個好 ..
時間:2025-05-22 10:25:03
石家莊人民醫學高等專科學校對比湄洲灣職業技術學院哪..
時間:2025-05-22 10:22:03
 2025年最新大型紀錄片《一帶一路》觀后感范文
2025年最新大型紀錄片《一帶一路》觀后感范文 2025年最新微電影《長征在路上》觀后感
2025年最新微電影《長征在路上》觀后感 2025年最新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微電影長征在路上觀后感
2025年最新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微電影長征在路上觀后感 2025年最新家庭教育紀錄片《鏡子》觀后感范文
2025年最新家庭教育紀錄片《鏡子》觀后感范文 2025年最新動畫大作《聲之形》觀后感
2025年最新動畫大作《聲之形》觀后感 貴州高考理科347分排名多少 排名多少位次
貴州高考理科347分排名多少 排名多少位次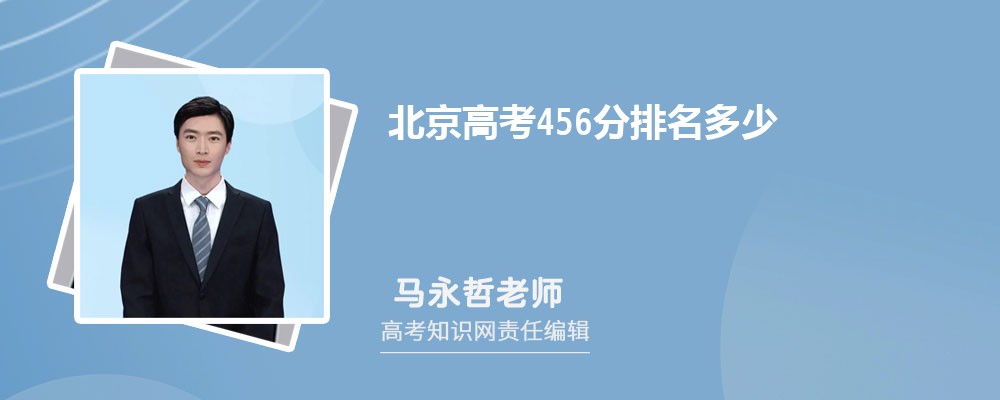 北京高考456分排名多少 排名多少位次
北京高考456分排名多少 排名多少位次 濟南職業學院對比遼寧機電職業技術學院哪個好 附分數線排名
濟南職業學院對比遼寧機電職業技術學院哪個好 附分數線排名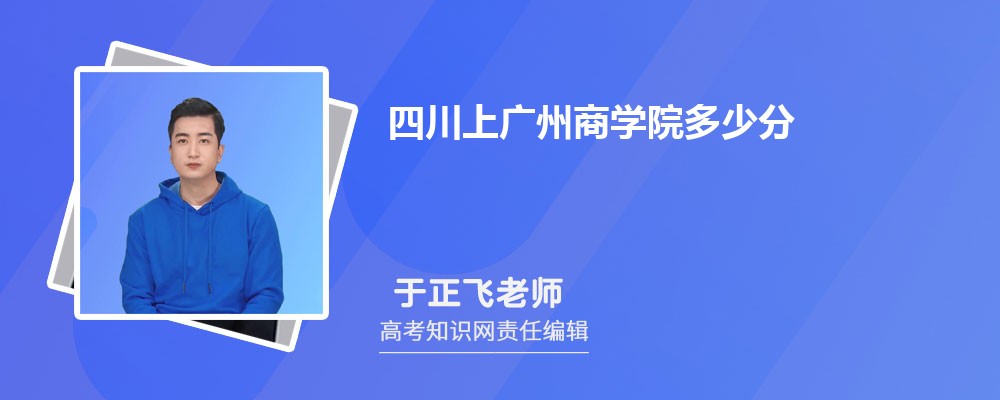 四川上廣州商學院多少分 分數線及排名
四川上廣州商學院多少分 分數線及排名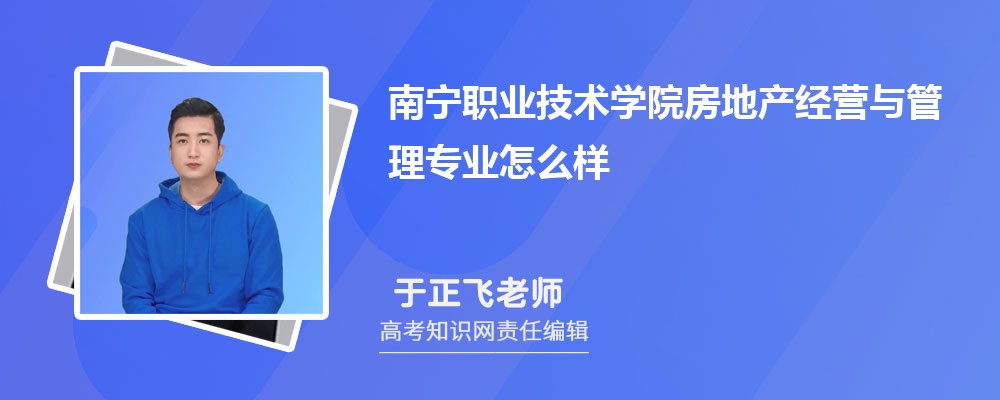 南寧職業技術學院房地產經營與管理專業怎么樣?錄取分數線多少分
南寧職業技術學院房地產經營與管理專業怎么樣?錄取分數線多少分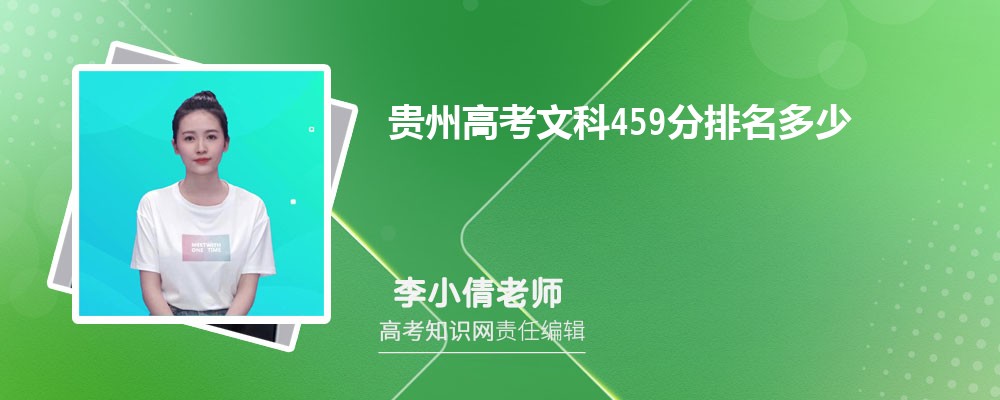 貴州高考文科459分排名多少 排名多少位次
貴州高考文科459分排名多少 排名多少位次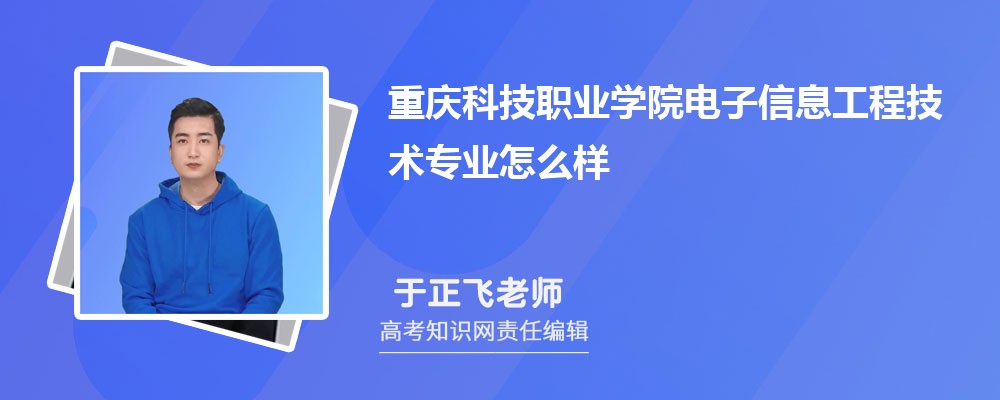 重慶科技職業學院電子信息工程技術專業怎么樣?錄取分數線多少分
重慶科技職業學院電子信息工程技術專業怎么樣?錄取分數線多少分 2025年貴州師范大學求是學院錄取結果查詢時間及錄取通知書發放時間郵寄..
2025年貴州師范大學求是學院錄取結果查詢時間及錄取通知書發放時間郵寄.. 貴州師范大學求是學院2025級新生在哪個校區,新生開學報到時間安排
貴州師范大學求是學院2025級新生在哪個校區,新生開學報到時間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