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黃州到澳洲,在文學的海洋中神游
更新時間:2023-08-25 12:12:10 高考知識網 www.comonvc.cn歐陽昱是旅澳學者、作家、翻譯家,現為上海對外經貿大學“思源”學者兼講座教授。歐陽昱在與江少川的對談中,回顧了個人的成長及創作歷程,表達了作家的文學觀與創作觀,對小說、詩歌與雙語寫作都發表了獨到新穎的見解,并就自己的幾部中英文長篇與詩集,談到如何突破文體束縛、甚至顛覆傳統寫法,而力圖創新的思考與探討。
關鍵詞:訪談;歐陽昱;雙語作家;文學觀;小說與詩歌
中圖分類號:I0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0677(2018)1-0046-07
江少川:對新移民作家,讀者往往想了解作家的經歷,先從你的家鄉黃州說起吧,在家鄉,上小學、中學的童年與少年時代,有什么比較深刻的記憶嗎?
歐陽昱:其實,我對“新移民作家”這個詞有些不太慣,或者說不太能夠接受。從國籍上講,我是澳大利亞國籍。我原來有個個人網站,在上面我稱自己是“an Australian poet and novelist”(澳大利亞詩人、小說家)。現在雖然該網站已經不再存在,但我依然是這么認為的。當然,國內的稱呼很多,除了“新移民作家”之外,還有“澳華作家”、“旅澳作家”等說法。對此,我也慣了,并不太在意。我現在更認為,我只是一個寫作者,其他的一切前置詞,對我都不適用。如果非要用,那就不妨用個比較準確的說法:旅華澳籍華人作家。
談起家鄉黃州,那是一言難盡的,幾本書都說不完。簡單來說,我在那兒出生、長大,讀完小學中學,18歲下放,才走出這個地方,以后基本上是在其他地方如武漢度過的,只是假期才回去。深刻的記憶有很多,具體說來就是,黃州的蘇東坡文赤壁、我父親的英語和多語以及詩歌的潛移默化的教育,以及初戀等。
江:你談到家庭教育與影響,說到父親的英語與多語水及詩歌創作,能具體談談父親對你潛移默化的影響嗎?
歐陽:我父親懂俄、英、德、日四國語言。解放前學的英語,解放后又自學俄語,我弟弟1980年前后到德國留學后,他又自學德語,為的是鼓勵二兒子學習,到了能夠和兒子用德語通信的程度。后來考高工,因為不滿英語考試中的種種弊病而決定自學日語,用日語而通過了高工考試。我想我讀大學時之所以除了法語之外,也自學了德語,還翻譯了一部德語小說,與這不無關系。我父親博古通今,特別了解古詩,很多古詩都能倒背如流。他給我起的名字,就是南唐李后主的“煜”,后來因大學一位登記學生名字的工作人員硬不相信有這個帶“火”旁的“煜”,而把我的名字弄成了“昱”。我對父親的一個深刻印象就是,任何時候都看見他坐在桌邊看書、記筆記。再不就是談古論今,無所不包。這對我的影響相當之大。
江:你的家鄉黃州有深厚的文化傳統,東坡赤壁為聞名中外的文學名勝,你自小自然非常熟悉親切,偉大的文學家蘇軾對你學文與有志于文學創作有哪些影響?
歐陽:黃州赤壁和蘇東坡,這是我記憶最深的文學之源。小時候不知有多少次跟朋友到赤壁玩,那時不收門票,隨時可以進入,常常晚上到那兒,以及旁邊的龍王山去玩。蘇軾在那兒流放四年的經歷,以及他在那兒寫下的名篇,都給我留下了刻骨銘心的印象。當然,還不止是黃州,還有長江對岸的鄂城(現在是鄂州),以及武漢和我下放的上巴河等地。
江:你出版中英文長篇多部,《東坡紀事》是唯一一部含有家鄉元素書名的長篇小說,遺憾的是沒有譯成中文版。少小離家老大回,出國多年重回故里,你是以怎樣的心態來寫這部長篇的,它表達了你對家鄉怎樣一種復雜的情感?
歐陽:《東坡紀事》就是蘇東坡對我的直接影響,書名即是對他的指涉,而黃州在我的書中成了“東坡市”。我在武漢大學的一位碩士研究生曾把該書譯成中文,但未譯完,也未發表。我1994年年底回國,因為要寫一本英文書。后來申請到一筆基金獎,就于1998年前后開始寫作該書,以莊道這個人物,至少表達了一種在國外待不下去,又不想長期回國的復雜心態。后來這個人物,還被我請回到英文長篇小說Loose: A Wild History(《散漫野史》)中,構成了另一種維度。
江:上研究生畢業后,到澳洲求學,后來怎么選擇移居海外,留在澳洲呢?初期是否也有一段艱苦拼搏的經歷?
歐陽:我在華東師大畢業后,其實沒有馬上去澳大利亞,而是到武漢大學教了兩年書,拿到博士獎學金后去的澳洲。1995年獲得澳洲文學博士學位后,我雖然有武大邀請回校的信函,但經綜合考慮之后,還是決定全家留在澳大利亞。開始并未料到生活之艱辛,相信有英文博士學位和驕人的成績(我博士論文的幾乎每一個章節,邊寫就邊在澳大利亞、新西蘭、美國和加拿大等國學術刊物發表),是不難找到工作的,但事與愿違,投函多少家大學,也有入圍十幾家,但都最終未果,從而決定走創作之路,而且是英語的創作之路,一邊通過自由寫作、自由翻譯謀生,一晃就是26年。
江:你上大學與讀研究生,專業是英美文學,后來怎么走上文學創作之路,而且走到現在搞創作與教學研究并舉,這樣會有矛盾與沖突嗎?
歐陽:其實我大學學的是英美文學,研究生學的是英澳文學,這導致我最后去的國家是澳大利亞。這是一。其次,我的創作之路早在大?就開始了。實際上,我現在能夠找到的最早一首中文詩,寫于1973年3月20日,也就是我還未滿18歲的那年。下放農村后,也寫了不少詩,而且創作了很多歌詞和歌曲,當時我的興趣其實在歌詞歌曲的創作方面,但因無人引路,中途夭折。上大學后,我開始大量寫詩和小說,根據自己現在正在編輯的80年代詩歌,估計超過上千首(這還不包括英文原創詩),所寫的小說散文文字,也超過了百萬字,但直至我1991年4月出國,我僅在《飛天》雜志發表了一首詩,即《我恨春天》,所有投稿均遭退稿。有意思的是,我很多80年代寫的詩,30多年后都在國內雜志上發表。因為我拿掉了寫作日期,編輯只能根據詩歌內容來判斷其好壞。
我現在的教學主要內容是英文創作和翻譯,這與我的寫作不僅沒有矛盾和沖突,反而相得益彰。例如,我的《譯心雕蟲》這本書,其內容有很多就來自我的教學和我本人的翻譯經歷,而且,我的英文詩歌和中文詩歌,不少材料直接來自教學。我有一類詩歌自稱“教學詩”和“翻譯詩”,據我所知是國內詩壇罕見的,都是我在擴展題材方面作出努力的結果。還有一些研究文章(中文和英文的),也都來自我的教學和翻譯經歷和經驗。
江:《淘金地》是你在國內出版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在國內引起廣泛關注,可以說是你在國內最有影響力的一部作品,就我的閱讀范圍而言,這部小說也是澳華文學中第一部寫華僑先輩淘金的長篇,談談是什么觸發你想到寫這部長篇,以及創作這部作品的感受。
歐陽:這部小說原來不叫《淘金地》,而叫《柔埠》。出版社為了市場,而把書名改成了現在這樣,當然也是得到了我同意的,盡管我直到現在仍然喜歡原來那個標題,因為那是Robe這個海濱城市的譯音。正如該書所講述的,1850年代有大批華人來澳洲淘金,但因遭到澳大利亞政府歧視,要收取他們每人十澳鎊的人頭稅(這個費用相當高,當年差不多可以使一個人傾家蕩產),于是他們乘船到南澳的Robe市,因為南澳沒有這個歧視政策,從那兒肩挑手提,一路步行五六百公里,到維多利亞省的幾個金礦淘金。這是一個廣為人知的故事,也跟我的博士論文有關,因為我研究的是1888-1988一百年澳大利亞小說中的中國人形象(該書即《表現他者:澳大利亞小說中的中國人:1888-1988》的中文版2000年在中國出版,英文版也于2008年在美國出版)。博士論文完成后,我心里一直想寫一本跟澳大利亞華人先輩有關的作品,一直沒有找到合適的題材,但2012年下半年我到上海任教后,開始聚焦這個題材。這時,我的寫作方式已經與之前有很大不同,幾乎完全從想象入手,向想象挑戰。例如,當我寫下第一章的“你”這個字時,腦中一片空白,并不知道自己要寫什么,但吊詭和奇異的是,兩三個小時后,筆下(鍵下)就自然、自動地生成了幾千字的文字,其后各章,也基本如此。可以說,這部小說幾乎完全是這樣產生的,以至于我告訴自己:不要低估自己的創造力,要不斷對它進行開發和挑戰,其潛力幾乎是無限的。當然,我也做了必要的資料調研等工作。
江:《獨夜舟》與此前中文長篇相比,不僅容量厚實,篇幅更長,你還有意識地在進行多種探索,有意突破長篇小說的寫法,請你談談在跨域題材、文體交叉、運用新手法等方面的思考。
歐陽:長期以來,我寫英文小說,從來都是失敗的,因為我始終把獨創性、先鋒性、實驗性放在第一位。這導致我的第一部英文長篇The Eastern Slope Chronicle(《東坡紀事》)遭全球28家出版社退稿,但最后被第一家退稿的出版社出版,一經出版,就獲得南澳的一個文學創新獎。記得當時和我一起入圍的還有諾貝爾獎獲得者庫切。我的第二部英文長篇(出版時已成第三部)The English Class(《英語班》)也是遭到十好幾家出版社退稿(記憶中是十八家),結果出版后獲得新南威爾士總督獎(社區關系獎的類別),并入圍其他四個文學獎。我的第三部英文長篇小說(后來先于《英語班》而出版)Loose: A Wild History(《散漫野史》),也是遭受無數退稿,最后出版雖未獲獎,也賣得不好,但有一位評論該書的澳大利亞書評家看后認為,如果要她推薦澳大利亞諾貝爾獎候選人,她要推薦三位,即Brian Castro,Gerard Murnane和Ouyang Yu。我無意在此自吹自擂,我只是援引一個事實,要說明的是,進行實驗性創作,是一件多么難的事。《獨夜舟》是我繼《淘金地》后,在中澳兩國創作的一部小說,其中的跨域寫作,既是我的親身體驗,也是我大腦中的交合,也應和了我后來的創作目標:寫到發表不了為止。道理很簡單:如果你想寫到能夠發表,那是最低要求,只要滿足一些既定的條條框框就行,只有寫到發表不了為止,你才能突破現有的所有套路,所有的成規,讓大腦和心靈真正自由起來,寫你想寫,寫你能寫。果不其然,這本書稿在國內沒有任何一家出版社接受出版,只能自己拿到臺灣出版。
江:《她》是你創作的第四部中文長篇,與前三部相比,這部長篇有何不一樣的與追求?封面上有“這是一部關于小說的小說”的題字,如何理解這句話。你在小說創作的跨界上,做了哪些方面的創新與實驗?
歐陽:我寫的數部中英文長篇小說,都是以男性為主人公的。一直有一個想法,想寫一個以女主人公為主的長篇,而這,就是《她》的創作初衷。一位女博士,把英年早逝的男友作品搜集起來,整理成書,為了紀念他而出版。它是一般的以故事為中心的小說嗎?我以為不是。它是通過作者想象的一位女主人公,對想象的作品進行重新整理、編輯、剪裁、細化、解讀和重置的故事,所以說是“一部關于小說的小說”。我想,這是一部討論記憶和失憶、原作和遺作、她者寫作和自我寫作、跨國界愛情寫作、原創和再創之間游戲關系等問題的作品。這是我的實驗。其創新之處(對我而言)在于,我找到了一種突破自己的方式。
江:你2017年新出版了第五部英文長篇小說《沈比利》(Billy Sing)。你是什么時候開始關注父親是中國人、母親是英國人而又生于澳大利亞的華裔沈比利的?又是出于什么機緣將沈比利的事跡寫成小說的?是否有計劃將其翻譯成中文,以讓更多中國人了解沈比利?
歐陽:今年出版的《沈比利》,其來源也與我的博士論文有關,那個時候我就注意到這位華人神槍手的事跡,但因謀生和其他原因而暫未進入。后來引起再度注意,也與澳大利亞一位白人導演拍他的一部電影有關。該導演啟用他自己的白人兒子扮演沈比利的角色,引起澳大利亞華人的強烈不滿。我決定寫一部關于他的小說,而且采取第一人稱,不僅如此,我還決定,不看該電影,也不看另一位白人所寫的沈比利傳記,而是通過自己的調研,像電影演員一樣進入角色。
我雖然把自己的英文詩歌翻譯成中文,又把自己的中文詩歌翻譯成英文,但我還是決定,不翻譯自己的英文長篇小說了,主要還是因為沒有時間。只能等以后有誰看中了再翻譯吧。反正這些都能等,我一點都不急。
江:學界有人把你的詩歌列為“口語詩”,?給你評了“新世紀中國百大口語詩人”獎,你認可嗎?你如何看待口語詩?
歐陽:陰錯陽差吧。我寫的是“口語”詩嗎?我的回答是:既是又不是。我80年代寫的中文詩,一直走的是反傳統、反朦朧詩、醉心實驗的道路。那時就開始實驗雙語詩(去年在澳大利亞還獲得一項資助,寫一本中英雙語詩,現在詩集已完成)、拼音詩、音樂詩、清單詩、方言詩、自動寫作詩、現場創作詩等。我以為中國目前的“口語詩”場域遠遠不夠寬泛,題材遠遠不夠闊大,語言遠遠不夠創新,走得實在還不夠遠。西方的口語詩(spoken word poetry),已經走向slam poetry(詩歌大滿貫)、performance poetry(表演詩)、sound poetry(聲音詩),conceptual poetry(觀念詩)等,把詩歌(包括口語詩)推向極致,這在中國幾乎沒有。而且,僅以口語詩來涵蓋一切,就像當年的朦朧詩一樣,鋪天蓋地而來,掩蓋遮蔽了詩歌的其他可能性,比如我現在所創作的詩歌,已經進入音樂詩、圖畫詩、聲音詩、現場拾得詩、概念詩(conceptual poetry)等。我不想被口語詩束縛,一旦束縛了,是很舒服,但人的創造力就被綁架了。而且,我對目前口語詩的這種稱王稱霸,打擊一切其他詩歌創作的作風是很不滿的。
江:你的第十部中文詩集《入土為安》,封面上有“一部不可能譯為任何文字的詩”,這句話的意思是只能用中文表達,許多詩人認為詩是不能翻譯的,可否從你豐富的中英、英中雙語詩歌翻譯經驗出發談談你的認識?
歐陽:其實,這部詩集的書名本來就一個字:《詩》,因為一整本書,其實就是一首詩,但又遇到了來自出版社的“建議”:詩這個字太多,容易重復。我這個詩人的胳膊,永遠拗不過出版人的大腿,最后還是從書里挑了一個改寫的成語,即“入詩為安”,將其作為書名。最,澳大利亞先鋒詩人A. J. Carruthers一看該詩集就說:這是conceptual poetry(概念詩)。所謂“概念詩”或“觀念詩”,簡言之,就是概念或觀念在先,詩歌由概念而生發,可以是詩歌“現成品”或詩歌“拾得”,或其他形式(詳見:https://en.wikipedia.org/wiki/Conceptual_writing )。我的這部詩集,前后寫了兩三年,均為腦中拾得、書中拾得、隨處拾得和成語拾得,并以“詩”字強行進入,同?參合以英語,部分成為雙語詩,無非基于一個很簡單的觀念,即詩無處不在。之所以稱之為“一部不可能譯為任何文字的詩”,是因為的確無法翻譯,如果不是處處要做腳注的話。借用我昨天跟Andy聊天時所說,我做的一切都源自于一個“against”(反)字。當科技使一切都變得容易時,作為一個詩人,他所要做的就是,使一切變得難起來,藝術之易,就在藝術之難。現在有了Google Translate,什么東西往里一放,眨眼就能成為想要的語言,但那種東西為我不齒,我要的就是against translation(反翻譯),也就是寫到無法翻譯的地步。否則人跟機器還有什么差別?
江:聽說你2017年要出版一套詩話集《干貨:詩話》,可否簡單談談此書?比如為何取名為“干貨”等等。
歐陽:對的,這本書寫得太久(六年多),也寫得太長(將千頁),導致我自刪了十多萬字,剩余的八百多頁,出版社建議分上下冊出版,否則一本出來,有一公斤多重,而且容易散頁。最后決定分上下冊出,上冊現已出版,下冊也會在2017年年底之前出版。所謂“干貨”,不妨借我本書上冊開頭的一段話來解釋一下:
干貨一詞,來源于一次講話后,伊沙對我發言那篇東西的評價:好,都是干貨。
它觸動了我。實際上,這是這么多年來,我寫作的一個動機:為不管給誰讀的人,提供一種扭干了所有水汁的干貨。把浪費讀者的時間最大限度地縮短。①
江:你的英文長詩《最后一個中國詩人的歌》(Songs of the Last Chinese Poet)在評論界廣獲好評。有一個細節特別想問你,全詩除了T.V., VIPs等極少數詞匯保持了應有的大寫形式外,每行詩首字母都是小寫,尤其是I全部以小寫形式i出現,而最后一句(THE WEST WILL WIN)又全用大寫形式。可否談談這樣做的深意?
歐陽:這首英文長詩,有三千多行,是我在讀博士研究生時創作的,寫了整整一年。剛開始定名為Songs of the Last Chinese Poet at the End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二十世紀末最后一個中國詩人的歌》),后來跟我朋友,澳大利亞小說家Alex Miller談起時,他說:干嘛不拿掉后半句?我一想,果然不錯,就留下了前半部分而拿掉了后半部分,因為都暗含在里面了。
你看得很仔細。全文小寫,原因有二。一是借鑒了美國詩人e. e. cummings的詩歌寫作方式。他的詩歌,包括他本人的名字,都無不小寫。其次,我的母語是中文,中文是沒有大小寫之分的。所以一律小寫。最得知,加拿大一位印度裔,名叫Rubi Kaur的90后女詩人,寫詩也一律小寫,因為其母語既無大小寫,除句號外,也無其他標點符號(詳見https://en.wikipedia.org/wiki/Rupi_Kaur)。這就是移民給移民國帶來的新的文字沖擊。
我記得,1990年代后期,我大量翻譯中國當代詩和中國古詩,也采取了小寫的方法。有一位澳大利亞白人翻譯,名叫Simon Patton的,后來也采取了這種方式,不知道是否受到我的影響,但再后來,我又放棄了這種方式。
其次,我最后那句“THE WEST WILL WIN”(西方終將勝出),全部大寫,是蓄意為之。全部大寫是強調,也是諷刺。結果產生了未曾預料的效果。我99年在北大住校時,有一位中國的研究生未看全書,只掃了一下最后一句,便很不高興,認為是我在歌頌西方。對此,我就懶得多言了。意思是,看了全書再說吧。
江:記得你在一篇訪談中說過“我寧可我的詩寫到此生完全不可發表的地步”,在《要失敗就失敗得更好:寫到發表不了為止》一文中更是鮮明地提出先鋒的三個意義之一就在于“寫發表不了的東西”。在一般創作者看來是噩耗的“發表不了”,在你這里卻成了對寫作的最高褒獎與肯定。你的這一認識究竟是怎樣形成的?
歐陽:這一認識,有個過程。記得在大學時,我有一個認識,東西要寫得讓人關注到評論的地步。現在看來,那是多么淺陋。寫到完全不可發表的地步,則是對詩歌自由的認識。我對詩歌的認識,就是一個字:freedom(自由)。如果一個如此被世人輕賤,幾乎與名利毫無關系的文學樣式(英文有句老話說:there is no money in poetry[詩無錢]),也要給它穿上三寸金蓮,五花大綁,削足適履地去適應各種刊物(包括中國和世界其他各地的刊物)的條條框框,那還不如不寫。我創作的英文詩歌,從一開始就遭到無數退稿,而最終發表時,往往在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后。這也說明,我在寫作時,是不以發表為終極目的的。唯有這樣,才能隨心所欲地表現自己的和感情。其實,即便此生不能發表,來世再發表也不遲,這樣的先例不是很多嗎,如狄金森、卡夫卡、佩索阿等。再說,很多暫時發表不了的作品,后來還是發表了(蒲松齡的《聊齋志異》至少是在他去世50年后才出版的:https://baike.baidu.com/item/蒲松齡/28998?fr=aladdin),而且得獎,是不是也說明不為鉆圈套而寫作,有自身的道理在?
江:在海外作家中,能同時用中英文創作小說與詩歌,且多產的人,的確不多,請你談談,你在創作小說與詩歌時,有怎樣不同的心境或曰心態?
歐陽:簡單說來,我是一個在寫作中經常跨界的人,如此一來,我的詩歌寫得像小說,小說寫得像詩。我2005-2008在武大任教期間,拿到一筆創作基金獎,創作我的The Kingsbury Tales(《金斯勃雷故事集》),寫得停不下來,總共寫了600多首,最后雖意猶未盡,但還是命令自己停了下來,有一種非常舍不得的感覺。這是我出版最順利的一本詩集,一申請,就拿到基金獎,一投稿,就被出版社接受出版,而且我用的書名也不同一般,雖然都是詩,但書名是The Kingsbury Tales: A Novel(《金斯勃雷故事集:一部長篇小說》)。唯一的遺憾是,出版社只出一百頁,收入80來首詩。后來我干脆自費出版了The Kingsbury Tales: A Complete Collection(《金斯勃雷故事集全集》)(將600頁,自我刪除了若干首)。另外就是,我曾認為,長期生活在一種語言中,對人是有害的。例如,我長時間寫英文?,回頭再寫中文,會發現很陌生,下筆用字,都會出現迥異于常的奇特現象,特別有利于創新。比如,我在《把》這首詩中,就生造了相對于“母語”的“父語”一詞,以及其他詩中的“李白不白”等語句。我喜歡在這種語言混雜的狀態中著意出新。實際上,每每聽到“不忘初心”一詞,我總聽成“不忘出新”,那才是我的創作宗旨。
江:不論是讀你的小說還是詩歌,除了感到在藝術先鋒性、語言陌生化等方面的驚喜之外,還往往在層面受到猛烈的沖擊。比如在小說《憤怒的吳自立》里,就可以在吳自立身上看到西方大哲尼采的影子。請問你的深度是怎樣得來的?有沒有特別受惠過的哲學家、家?
歐陽:《憤怒的吳自立》我寫于1989年,之前已經準備了兩年,于1989年6月4日晚上,在上海華東師大正式動筆,因為這是我在該校讀研的最后一年。當全校的學生都圍著電視觀看天安門發生的事情時,我獨自一人在階梯式教室后面開始了這本書的寫作。其實,里面大量采用的材料,都來自我大學時期的寫作。我只不過是重新經過了虛化的整理而已。我大學畢業后當了幾年翻譯,接觸了不少外國專家,特別是來自美國的專家。記得有一位姓Miller的美國專家回美國之前,我專門讓他給我寄幾本叔本華和尼采的著作。他沒有爽約,很快就給我寄來了我心儀的兩位哲學家的英譯作品,讀后給我影響很大,特別是其厭世的哲學觀。給我影響很大的其他作家還包括英國的哈代、吉辛,德國的黑塞、歌德、海涅,奧地利的茨威格、卡夫卡、伯恩哈德,美國的海明威、梭羅、愛默森、金斯堡,法國的雨果和法郎士,葡萄牙的佩索阿等。對其他作家、詩人、哲學家、家,我多有涉獵,但不拘泥一人,而是博采眾長,廣泛吸收。關鍵還是以己為本,進行獨立的思考和觀察。
江:在海外作家中,用雙語創作的作家雖然不少,但同時用中、英語創作多種文體,如小說、詩歌等,并大量翻譯西方文學名著者卻不多。據統計,至,你的中英文原創作品及譯著總計達84種,可謂多產驚人了,你是如何處理工作與寫作的關系、如何處理讀書與寫作的關系的呢?你有何寫作慣?
歐陽:實際情況是,截止2017年10月23日,我的出版清單上,出版書籍達到了92本,而且未計所編的書。寫作和翻譯,就是我生命的一個部分。我的寫作,滲透到我的工作(包括教學、筆譯、口譯、講學、旅行等),無時不刻在寫作,甚至在朋友請去唱K時,我也不唱歌,而是寫詩,并發現這可能是最好的一種寫詩方式,非常能夠激發創造力。幾乎每上完一節課回來(包括上課時),我都會寫幾首詩,而我的讀書是見縫插針式的,只要有一點時間,我就會讀書,在搭車、搭飛機、在法庭做翻譯(這往往是讀書寫詩的最好地方,因為等待開庭,往往一等就是一整天,我是說在澳大利亞)等,我都會擠出時間看書,每年中文英文的書籍,至少要各看七八十本。家里的圖書大量堆積,導致內人總有怨言。我現在無論看書還是寫書,也與以前有很大不同,我會同時看六七本書,同時寫六七本書。記得我現在教的研究生,看書極慢,一本書要看幾個月。我跟他們分享我讀博士時的經驗,那時,我一天可以看十幾本書,經常是厚達五六百頁的書。我的寫作慣,讀博時(二十多年前)基本都在晚上,一寫就到深夜,不到一點半不睡覺,天天如此,一直這樣了二十年。現在我不那么做了,因為太傷身體。現在我主要上午寫詩,因為早上起來后,總是詩潮如涌。每天至少三到五首。2012年到在上海教學期間,每年至少要寫1200多首詩(還不包括英文詩)。這二十多年在澳大利亞,我至少寫了上萬首詩(家里寫的詩多得占去了太多的位置),以至于最后干脆決定不再把每首打印出來,以免占據更多地方,而是直接存在電腦中。如果創作長篇,我會把它放在第一位,一切次之。不過,一有感覺,我就會當時當地寫下來。我在澳大利亞上寫作課時對學生說:寫詩要趁鮮,就跟做愛一樣,是不能等的。
江:與上面的問題相關,而且讀者很感興趣的是:用不同的語種,如中文與英語進行創作,在取材、立意、思維方式上有什么不同嗎?
歐陽:這個問題,也是澳大利亞讀者經常問我的一個問題,他們甚至會問:你是不是一邊寫,一邊翻譯?據我所知,有些華人作家就是這樣的,比如我當年采訪的一位原先來自新加坡,后來住在悉尼的華人女作家Lilian Ng,就是把話先想好,在腦中翻譯后,再用英文寫出來的。對我來說不是如此。我們那個時代讀大學(1979-1983)學英文,最高的要求就是,要用英語思維,這給我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因此大學時代就用英文寫作詩歌,研究生期間也是如此,1991年到澳洲后,我便開始英語詩歌寫作,博士論文寫完,我已經出版了第一部英文詩集Moon over Melbourne and Other Poems(《墨爾本上空的月亮及其他詩》,1995)并寫好了上面所說的《最后一個中國詩人的歌》(1997年出版)。意思是說,對我來說,不存在這種腦中翻譯的狀態,一切都是直接轉換的,仿佛我就是一個說母語者。至于在取材和立意上,我想我還是寫跟自己身世、跟華人有關的題材多,但我很早就看到,這是一個問題,因此,我也有意在小說和詩歌中寫入除華人之外的其他人種,如《英語班》中京的白人太太和白人岳父,記得我的澳大利亞白人文學經紀人Sandy看后,說很喜歡我寫的那個白人岳父。這對我來說是一種挑戰,但我喜歡這種挑戰,而不想一味地只做中國菜給西人吃(關于此說,可參見我的一篇文章,《告別漢語:二十一世紀新華人的出路?》
中國點擊率最高的一篇文章 !2023-08-13 03:45:29
貴州高考理科347分排名多少 排名多少位次2025-05-22 11:00:51
北京高考456分排名多少 排名多少位次2025-05-22 10:57:01
濟南職業學院對比遼寧機電職業技術學院哪個好 附分數線排名2025-05-22 10:54:45
四川上廣州商學院多少分 分數線及排名2025-05-22 10:51:12
南寧職業技術學院房地產經營與管理專業怎么樣?錄取分數線多少分2025-05-22 10:48:48
貴州高考文科459分排名多少 排名多少位次2025-05-22 10:45:57
重慶科技職業學院電子信息工程技術專業怎么樣?錄取分數線多少分2025-05-22 10:42:15
澳籍華裔女作家蘭子出版長篇小說《姐姐》2023-08-18 15:25:07
孔夫子的三條精神出路2023-08-25 03:07:48
基礎寫作教學中賦形模型與創意模型的融合2023-08-25 20:53:55
澳籍華裔女作家蘭子出版長篇小說《姐姐》2023-08-18 15:25:07
孔夫子的三條精神出路2023-08-25 03:07:48
李雪濤:詩人筆下的身份認同2023-08-26 05:34:39
精品文章
- 1千古才女最消魂 《多少事,欲說還休..2023-08-20 05:34:32
- 2《囚綠記》“釋綠”情感與心理探因2023-08-23 22:58:14
- 3任中敏《白香詞令》輯存2023-08-17 12:24:32
- 4明末浙東流亡海外遺民詩歌研究2023-08-17 17:23:24
- 5淺析豐子愷作品中的飲食文化2023-08-16 07:57:59
- 6中國現代格律詩的發展及展望2023-08-20 18:56:55
- 7張大千詩詞創作的巴蜀情懷原因探究2023-08-16 06:52:19
- 8《弟子規》在大學生社會主義核心價..2023-08-21 11:04:25
- 9多種語言學習中跨文化交際意識和能..2023-08-23 08:04:54
- 10《八仙出處東游記傳》中八仙廣泛流..2023-08-20 21:00:30
圖文推薦

內蒙古高考500至530分左右可以上什么大學
時間:2025-05-22 10:39:38
內蒙古醫科大學對比河北環境工程學院哪個好 附分數線排..
時間:2025-05-22 10:36:19
湖南高考歷史565分排名多少 排名多少位次
時間:2025-05-22 10:32:43
湖北民族大學法學專業怎么樣?錄取分數線多少分
時間:2025-05-22 10:28:51
天府新區航空旅游職業學院對比泰山職業技術學院哪個好 ..
時間:2025-05-22 10:25:03
石家莊人民醫學高等專科學校對比湄洲灣職業技術學院哪..
時間:2025-05-22 10:22: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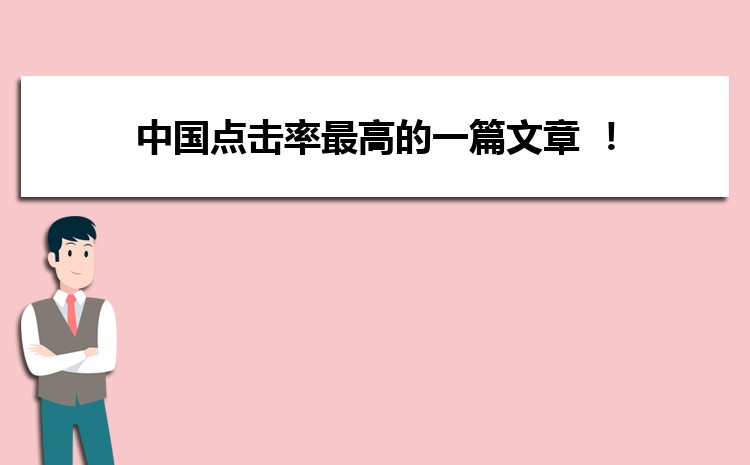 中國點擊率最高的一篇文章 !
中國點擊率最高的一篇文章 ! 貴州高考理科347分排名多少 排名多少位次
貴州高考理科347分排名多少 排名多少位次 北京高考456分排名多少 排名多少位次
北京高考456分排名多少 排名多少位次 濟南職業學院對比遼寧機電職業技術學院哪個好 附分數線排名
濟南職業學院對比遼寧機電職業技術學院哪個好 附分數線排名 四川上廣州商學院多少分 分數線及排名
四川上廣州商學院多少分 分數線及排名 南寧職業技術學院房地產經營與管理專業怎么樣?錄取分數線多少分
南寧職業技術學院房地產經營與管理專業怎么樣?錄取分數線多少分 貴州高考文科459分排名多少 排名多少位次
貴州高考文科459分排名多少 排名多少位次 重慶科技職業學院電子信息工程技術專業怎么樣?錄取分數線多少分
重慶科技職業學院電子信息工程技術專業怎么樣?錄取分數線多少分 澳籍華裔女作家蘭子出版長篇小說《姐姐》
澳籍華裔女作家蘭子出版長篇小說《姐姐》 孔夫子的三條精神出路
孔夫子的三條精神出路 基礎寫作教學中賦形模型與創意模型的融合
基礎寫作教學中賦形模型與創意模型的融合 李雪濤:詩人筆下的身份認同
李雪濤:詩人筆下的身份認同